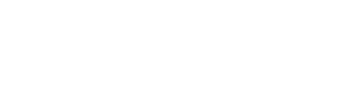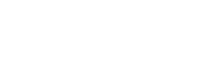陶斯亮:忘了没有,“希波克拉底誓言”[爱尔公益]
2019-07-17 20:09栏目:文教
前些日,网上读到一位北大急诊科医生的文章,写了他与一位患者十年的结缘。医生以朴实又有温度的文字,写了他与一位烧伤老人从最初的就诊到十年后的再次见面,医者崇高的使命感与无奈,患者的求生欲与终因贫穷的放弃,使读者为之动容。此文也获得网友一片赞誉之声。在医患关系日益恶化,各种超出人们想象力的医患矛盾,以及残忍暴力层出不穷的当下,能读到这样一篇文章,犹如从污浊空气中吸到一股新鲜的清气,在人性荒芜的沙漠中吮到一口甘霖,弥足珍贵!(作者:陶斯亮;来源:爱尔公益)
我是学医的,又当了20年的临床医生,1987年脱离专业改行。我之离开,完全出于一时的任性,但我的内心一直保留着对医生的眷恋,保留着当医生时的记忆。
我们那会儿,病人以性命相托,医生以心承诺,压根儿就没有“医患矛盾”这个词,说的最多的就是“救死扶伤”。北医急诊医生的文章,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历经了半个世纪尚未遗忘,连我自已都感到意外。
我一入学,首先是接受“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教育,“一切为病人,病人至上”是那时的金科玉律,在校园里、医院里处处体现。我的老师,上级医生,同级医生,护士甚至行政干部,无一不在用行动体现着这种精神。置身其中,我不能有丝毫懈怠,说几件当年当医生时的回忆吧!

陶斯亮在第二军医大学(现海军军医大学)时期
也是在当实习医生时,我分管的病房收进了一个“厌食症”患者,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上海人,看上去不到二十岁,白白净净,眉清目秀,但就是不能吃东西,一吃就呕吐,以至看见食物就恶心。他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完全是神经官能症。他入院时已是形销骨立,天天输葡萄糖白蛋白,但谁都知道这仅仅是安慰治疗,病人最后只能是饿死。这么年轻,又是大学生,如此结局太残酷,于是我决定试试我的办法。每天晚饭后,我在口袋里放一个桔子,一根香蕉,再用轮椅推他出来,哪儿热闹去哪儿。他喜欢看排球赛、篮球赛,趁他看的入神时,我往他嘴里塞一瓣桔子,或一小段香蕉,他下意识的就吃下去了。我不动声色,天天傍晚推他出来看热闹,时不时往他嘴里塞点吃的,到后来干脆放一个桔子在他手上,直到一天,他举着吃剩半根的香蕉,疑惑的看着我,我才笑着说“谁说你不能吃东西?你这不吃的挺好吗!”此后病人再无食道异物感,开始进流食,半流食直至正常饮食。出院后不知这位病人是否重返校园,后来的命运又如何?我们是同龄人,如果他的“厌食症”果真治好,那么此刻,他是否如我一样共赴残阳,享受天伦之乐呢?
文革中,我被分配到遥远荒僻的甘肃临夏解放军第七医院当医生。这是个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有回,藏,东乡,保安等多个少数民族。我们虽是军队医院,但也常常要收治危重的少数民族病人。记得有天从甘南藏族自治州送来一位藏族妇女,患的是急腹症,生命垂危。但当把她推进走廊时,她拼足全部力气撑起了上半身,只见她双眼发光,惊叹道,“多美丽的房子啊!” 其实七院是野战医院,非常简朴。但几辈子住帐篷的藏胞,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白的墙。她后来死了,死在四面白墙的病房里,她走的安祥,因为这白色的病房就是她心目中的天堂。整理床铺时,看到满是虱子,只能将全部卧具烧掉。那时给老乡看病,我们都得额外把袖口匝紧,就这样每晚睡觉时仔细查衬衣,总能发现一两个又肥又大的虱子。但虱子并不妨碍我们对病人的热情服务和精心治疗,我们不会离病人远远的,而是经常手拉着手,抚摸着患者头发,耐心的说啊说!有次一位大娘特意爬起来看着我,“闺女,你说话真好听!” 这就是我们内科医生的基本功——话疗。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发生在我当“空军总医院”主治医师时。一天,病房收进了一名战士,高烧不退,身上鼓起一个又一个的脓疱,用什么抗生素都无效,经过协和医院专家会诊,确诊为极为罕见的“脓疱症”。这是一种如“红斑狼疮”般的免疫性疾病,需用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但病人身上有大小十几处切口,由于用激素难以痊合,形成了一个个溃疡,这让病人很痛苦也很危险。请外科医生来换药?口都张不开,让下级医生干?有推脱苦活累活之嫌,我决定自已换药。我每天跑到外科大楼去借换药包,给病人彻底消毒清创,再洒上生肌散,盖上干净纱布。就这样,忙活了一个月,终于在病人仍在使用激素的情况下,所有切口都愈合了。这名战士最后治愈出院了,协和医院的专家说“你能这么坚持换药,不容易啊!”

陶斯亮在空军总医院时期
近些年偶尔回下“空总”,与当年几位老同事议论当下的医患矛盾,当我为“杀医现象”愤愤不平时,却听他们说“陶医生,现在的病人不是咱们那会儿时的病人,医生也不是咱们那会儿时的医生了!”,我有点懵,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何时开始的?”……是呀,医患关系是从什么时候起变坏的?又是为何原因?难道仅仅是因重商主义引发的吗?不必否认,现在的医生服务态度和质量比不上他们的前辈,我都有过体会。一次我老头千转百寻挂了一家名医院的专家号,专家草草看了一眼片子,又问了一下我老头的年龄,然后说了句“这么大岁数了你就凑合着活吧!” 气的我老头发誓再不去这家医院看病。但换位想一下,现在的医生,圧力比我们那会儿大的多得多,你看三甲医院门诊楼里那乌泱乌泱的人群,每个医生被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着,他纵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呀!我认识的一位年轻医生说,看头十名病人头脑是清楚的,二十个以后就烦躁了,到了五十就变得麻木了,可我们的医生往往一天要看七八十甚至上百个病人,这时的医生应该是脑子一片空白,只是躯壳在机械的应对病人,那看病质量可想而知了。加之现在的病人戾气很重,动不动就骂医生打医生,甚至刀捅斧砍医生的事也频频发生。这种情况下,这“医患矛盾”怪谁呢?如果公平客观说,只能怪医疗资源极大的不公。

陶斯亮(左二)与空军总医院的同事们
如果能让医生从容的看病,哪一个医生不想当白求恩?如果每个病人都能得到医生至少三分钟以上的问诊或一张笑意盈盈的脸,又有哪个病人愿意闹事呢?所以“医患矛盾”,根子不在医也不在患,而在于医疗制度的不公。
每个医生在入职前,都要做“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请求神祇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作者:陶斯亮;来源:爱尔公益)
如今,我们忘了没有,这神圣的誓言。作为曾经的医生,我没有忘记,我的医生朋友们,他们也永远不会忘记。